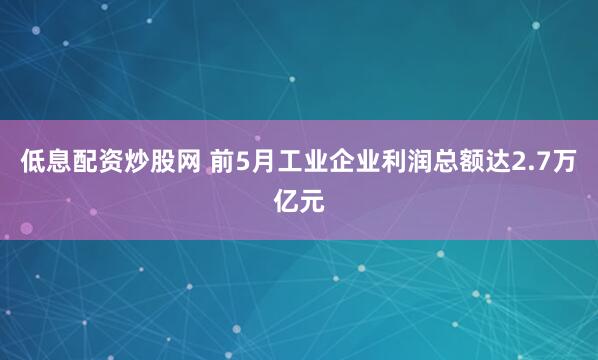解放战争期间配资实盘证券配资门户,我军出现了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尽管一些高明的战术并未经过系统的推广,各大战略区的高级指挥官们却几乎在无形中同步运用了这些战法。毛主席开创的战略分散牵制战术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学术界对这一战术并无专门的命名和详细论述,现有的称谓难免显得不够精准。笔者能力有限,暂时也难以找到更为专业且一目了然的术语。以更通俗的表达来说,这种战术可以形象地称作“极限拉扯战术”,它强调在战场上最大限度地牵制和分散敌军兵力。
一、独特的秘诀
极限拉扯战术具体指什么?1947年3月,关于陈赓兵团是否应入援陕北的争议,就是此战术的典型案例。胡宗南率领约二十万兵力在陕甘宁地区追击我西北野战军。相比之下,彭德怀直接指挥的部队仅有2.8万人,兵力对比极为悬殊,令人感到压力巨大。
中央曾考虑让陈赓兵团增援陕北,但最终未采纳这一方案。这个决策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远非《三国演义》中诸葛亮那种算无遗策的神机妙算。最初,中央打算让陈赓纵队从晋南和豫西北稍作后撤,转而在晋西南黄河和汾河之间的三角地带展开重点进攻,牵制胡宗南军队侧翼。
展开剩余86%中央本意是陈赓纵队逐步向陕北靠拢,以加强那里的兵力应对胡宗南。然而,陈赓纵队在晋南大规模作战,效果竟然比直接进入陕北更为显著。这样一来,胡宗南军队不仅要正面追击西野,还得分心防范陈赓的夹击,两面夹击令其陷入两难。
我军通过这两处分散部署的四万多兵力,成功拖住了敌方十几万主力,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战术效果。毛主席从中获得了启发。1947年6月20日,他致彭总的电报中,首次提出了陈赓纵队与西野主力分开行动的思路,并引入“战略分散牵制战术”的概念,特别强调了分开行动既有远距离也有近距离两种形式,具体如何实施要视战场情况而定。
随后,7月21日召开的“小河会议”上,毛主席正式决定陈赓兵团不再进军陕北,而是继续向南运动,战略上牵制胡宗南,而不与西野集中兵力。此举看似与我军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传统原则相悖,实则体现了战略牵制与战术集中之间的辩证统一。集中与分散各有利弊,究竟何时集中何时分散,需结合实际灵活运用。
有趣的是,毛主席虽未将此战术形成全军统一推开的明确结论,但各大战区高级指挥员们却几乎自发学会并灵活运用。
二、陈云:一法通万法
陈云坚决主张保卫南满,也是极限拉扯战术的典范案例。之所以先提陈云,是因为他特殊的身份——一个公认的“书生”、文职领导,毫无军事指挥经验,却能在关键时刻与毛主席的军事思想高度契合。
1946年底,国民党军对南满根据地发动进攻。东北我军分为北满、南满和西满三部分。国民党军从最弱的南满先下手,意图一举拿下。南满仅剩四县地盘,兵力只有两个纵队,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内部发生激烈争论,不少人主张放弃南满,渡松花江与北满部队会师。
这种“打不赢就撤退”的惯例策略,在敌强我弱情况下确实合情合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但陈云和萧劲光没有照搬旧法。萧劲光虽提出坚守南满,但未能说服反对派,战事会议僵持至深夜,萧劲光只得请陈云出面做最后决断。
陈云以形象生动的比喻打动众人:把敌军比作一头牛,牛头和牛身向北满进攻,南满不过是牛尾巴,如果放弃这条尾巴,牛就会横冲直撞,南满失守,北满也将危在旦夕。这一论断鲜明诠释了极限拉扯战术的精髓。
随后,南满展开了著名的“三下江南”和“四保临江”战役。虽然从军事角度看,四保临江战果有限,根据地面积未显著扩大,但其战略意义非同小可。以有限兵力占据重要地理位置,多点牵制敌军,使国军顾忌重重,难以集中优势兵力作战。
陈云作为经济工作的宗师级人物,却能迅速领会并贯彻毛式军事思想,体现了“一法通万法”的哲学境界。经济与军事虽属不同领域,但都遵循一些共通的规律,尤其是在战略层面上的大局观和灵活应变能力。陈云的成功,离不开他深厚的大局意识和在绝境中培养出的临机调整能力。
不过,陈云不擅长末端具体的战术指挥,若由他亲自指挥四保临江战役,极可能出现问题。幸亏有萧劲光、韩先楚等人具体负责,才保证了战役的成功。
三、粟裕:深研应用,多场景复刻
粟裕以善于打奇袭著称,他的非凡军事思想与极限拉扯战术的运用密切相关。解放战争初期,华中与山东两大战略区在是否坚持苏中或北撤山东问题上曾有激烈争议。即便粟裕带领苏中七战全胜,这种分歧仍未消除。
山东方面频繁向华中请求增兵,想集中力量在津浦路展开作战,但粟裕坚决反对不断抽调华中主力,主张保持战略区完整性。1946年8月1日,粟裕在致中央的电报中明确指出,战略上应相互配合,但战役上不应强求完全配合,单独作战必须依靠自身力量解决面前的敌人,否则会影响其他战略区的机动能力。
在粟裕坚持下,苏中战略区基本保持完整,占据两淮富饶地区,不仅利于补给和兵员招募,也阻断了国军与山东的联系,战略作用显著。尽管后来国军在苏北、鲁南和苏南发动多线进攻,形成三线夹击,华中野战军最终不得不北撤,放弃苏中,但这并非粟裕战略判断失误,而是由于华中战略区牵制力不足所致。
转战山东后,粟裕多次尝试复刻极限拉扯战术。孟良崮战役中著名的“耍龙灯”战术广受军迷热议,而攻克泰安之役更能体现这一战术的精髓。深入研究战史可知,强攻泰安实际上违背了“耍龙灯”调动敌军、打乱敌方阵形的灵活原则。耍龙灯讲究快、灵、扰动,不能耗费重兵死守一城。
但粟裕巧妙地以轻灵策略掩护这场重兵突击,形成“奇正相参”的战术格局。泰安作为鲁中偏西的重镇,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北可牵制济南,南控鲁西南,西接运河。粟裕还在鲁西方向制造佯动,增强拉扯效应。攻占泰安几乎将鲁中战场分割为两部分,极大限制了国军的行动。
当然,国军经过孟良崮战役的惨痛教训,学乖了,遵循冈村宁次的建议,保持密集队形在鲁中山区坚守,尽管丢失一个整编师也不轻易撤退。孟良崮胜利原因复杂,不能完全归功于攻打泰安的战术,但该战术无疑对战局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豫东战役则达到极限拉扯的巅峰境界。陈唐兵团通过攻打开封掩护主力作战,战场重心转向睢杞,开封城攻下后又暂时放弃,攻守转换灵活自如。能把省会城市当作战略牵制工具,只有真正的伟人才敢如此放手,这种策略的魄力堪比放弃延安。
四、刘伯承:无形化用,神不知鬼不觉
刘伯承是我军杰出的军事理论家,与黄埔系不同,他擅长总结和研究战术,尤其能从理论层面把握各种战术的精髓并灵活运用。千里跃进大别山,是他的一次经典绝技,其历史意义无需多言。
当时刘伯承义无反顾地决定南下,既出于对中央决策的坚决服从,也反映了他对战略形势的深刻理解。一个奇特例子是“十一纵”的神秘表现。
刘邓大军在鲁西南作战时,先派王秉璋率第一旅渡黄河,成功吸引国军主力,为主力部队创造了战略空间。刘伯承看准这一点,将几个独立旅合编为十一纵,由王秉璋任司令。十一纵随即开启了传奇之旅。
在刘邓南下之际,王秉璋率十一纵突然北返黄河,制造出刘邓大军也将北返的假象。主力成功渡河南下后,十一纵继续在鲁西南地区灵活机动,时而与邱清泉第五军激战,时而袭扰其他国军部队,展现出极强的机动性和阻击能力,与华野十纵形成互补,令敌军极为头痛。
当时刘伯承在大别山只带了部分纵队,陈赓兵团仍在豫西,白崇禧在武汉调动大军准备剿灭大别山,兵力不足且不能召回十一纵,王秉璋只得继续坚守鲁西南。该地位于三路大军进中原的咽喉,战略位置极佳。十一纵时独立作战,时受华野临时指挥,配合粟裕完成多场关键战役,配合默契无缝,淮海战役期间亦在豫皖苏地区遥相呼应,发挥巨大作用。直至中野主力围歼黄维兵团后,十一纵才回归中野建制。
十一纵之所以战绩斐然,除指挥得当外,关键在于其处于极限拉扯的关键位置,成功牵制敌军并攻守兼备,实现战场环境的最大化利用。
五、东北战区:战绩虽佳但战术运用欠佳
最后谈谈东北战区,毛主席对此寄予厚望。客观讲,东北整体战绩辉煌,林彪、罗荣桓、刘伯承领导指挥得当,毋庸置疑。
但在极限拉扯战术的运用上,林罗刘三人特别是作为主帅的林彪,表现不尽如人意,甚至可以说兴趣不大。他们更偏好稳健打法,讲究充分准备后再开战,不轻易冒险、不追求出奇制胜。因此望洋兴叹于孟良崮和豫东那种险胜战例,未能复制类似的战术风格。
林彪等人的计算深厚,反攻期间多次取得胜利,犹如草原巨象,一步步推开国军防线,令敌人无力反抗。辽沈战役初期,林彪不愿轻易尝试战略奇招,认为稳扎稳打即可,即使长春暂时攻不下,时间拖长也没问题。尤其考虑到锦州防御坚固,若轻易进攻可能导致后勤断链,得不偿失。
这一思路本无错,但与伟人的大战略相比,缺乏灵活应变。如果按步就班推进,敌主力得以脱身,后患无穷。且战略奇招往往能以少胜多,将十万兵力的战斗效能放大至数倍。林彪等人对极限拉扯战术理解不够深入,限制了更大突破。
最后说说为什么极限拉扯战术未能广泛系统推广,虽为毛主席与各大战区高级指挥员共同认知,却没有统一行动。古代科学史上,周朝与古希腊分别独立发现勾股定理,牛顿和莱布尼茨各自完成微积分,科学发展往往具有规律性,人们在某一阶段自然而然地发现相似理论。军事科学亦然。
毛主席与各大战区高级指挥员长期交流,认知和思维趋于一致。在相似战争条件下配资实盘证券配资门户,不约而同形成了对极限拉扯战术的理解与应用,这种“各自为政又异曲同工”的现象,
发布于:天津市鑫盛优配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